 第一卷 第1章 替嫡姐洞房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
第一卷 第1章 替嫡姐洞房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
 第一卷 第1章 替嫡姐洞房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
第一卷 第1章 替嫡姐洞房 替嫡姐與權臣洞房後
冬至這日,汴京下了今年第一場冬雪。
城裏城外,四處白茫茫一片,氣溫極低,城道上行人凍得瑟瑟發抖。
徐望月在屋裏也冷得細細抖着。
她只穿了薄薄一層鴛鴦肚兜,站在屋子中間,背後那隻手從她的側臀,到腰肢,再到前胸,一路往上撫摸。
讓她覺得自己像個貨物一樣,任憑對方審視檢驗。
「膚如凝脂,手如白玉。」
「不錯,細嫩光滑,挺翹能生。」
粗糲的指腹傳來的不適感,讓徐望月忍不住打了個哆嗦。
下一刻,那根手指竟要伸進她的嘴裏檢查牙口。
她的丫鬟紅玉急紅了眼:「嬤嬤不帶這麼欺負人的,我家姑娘還未出閣,不是什麼可以買賣的外室,嬤嬤怎麼拿那些人牙婆子的手段用在姑娘身上。」
五福嬤嬤見狀,不但沒收手,反倒一手指頭捅進去,在她口中一頓好攪和。
語氣輕蔑:「那些外室都是什麼身份?你家姑娘要伺候的可是世子爺,自然要仔細些。」
「再說,姑娘家舌頭上的功夫也是伺候人的手段,夫人送來的春宮圖難道沒有認真看嗎?」
說到這個,徐望月臉上臊得慌,連忙用眼神示意紅玉不要多言。
默默忍下這位五福嬤嬤所有動作。
嬤嬤見徐望月逆來順受乖巧得很,心中更加得意:「只是這小腹,比我家夫人略粗了一點兒,今日就不要進食了,以免晚上侍寢世子瞧出來。」
「這才白天,一天不吃豈不是要餓壞我家姑娘?」紅玉急到想哭。
嬤嬤冷嗤:「能有機會伺候世子是多大的福分,只是不吃飯而已,瞧把你矯情的。今晚是多大的要緊事,關乎到整個徐府的榮辱,若是穿幫了連累夫人,到時候別說是吃飯,說不準把你們再送回莊子上發賣!」
徐望月捏着紅玉的手示意她不要多言,隨後語氣柔柔:「謝謝嬤嬤教誨,望月謹記在心,必然不辜負長姐囑託。」
見徐望月懂事,嬤嬤也作威作福爽了一把,心滿意足拉開房門。
門外呼啦啦冷氣夾雜着雪粒子呼嘯而入,刺到骨頭縫裏的寒意侵襲。
徐望月忍着,臉上一直帶着笑,直到五福嬤嬤身影遠去,這才上下牙齒顫抖着鑽進被窩裏,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,連衣服都來不及套上。
實在是太冷了。
京城最冷的時節,帶着紛紛揚揚的大雪,更是凌遲刮骨。
「他們這是不把姑娘當人。」紅玉連忙衝上去關了門,「早知道大姑娘也不是個好相於的,如今嫁入定北侯府更是一發不可收拾,姑娘為什麼要答應這一出,這以後的日子恐怕不好過。」
紅玉越說越哽咽,原以為大姑娘與夫人願意把把徐望月放出來算是苦盡甘來,沒想到是存着豺狼虎豹的心思!
他們家姑娘是側室生的,身份本就比不上嫡出的大姑娘,加上小娘早逝只留下孤女,在徐家就更加受人欺負。
徐家主母善妒,自小娘死後就將沈望月關在了院裏,從不許出門,下人剋扣用度是常有的事情,經常飢一頓飽一頓。
好在姑娘有福分,生得碧月羞花玲瓏有致的,倒也沒有因為吃不上飯而纖瘦。
身形也和大姑娘越發相似。
這到成了造就一切的根源。
大姑娘徐遙夜自小與定遠侯府長子裴長意有婚約,原本是一樁美談。
未曾想裴長意七歲那年在一日外出時突遭禍事,失蹤了十數年。所有人都以為裴長意死了,而這個婚約就變得尷尬起來。
未嫁過去死了夫君,是望門寡。
徐瑤夜嬌生慣養養大的,怎麼受得了這樣的名頭,這許多年都在想着怎麼退婚能不傷了定遠侯府的面子。
畢竟定遠侯是聖人親封的異性侯爺,開國功臣,一身戰功無人匹敵,能與他
 喪屍不喪屍 《喪屍不喪屍》是筆名叫隨便精心創作的科幻小說,聖墟中文網實時更新喪屍不喪屍最新章節並且提供無彈窗閱讀,書友所發表的喪屍不喪屍評論,並不代表聖墟中文網贊同或者支..
喪屍不喪屍 《喪屍不喪屍》是筆名叫隨便精心創作的科幻小說,聖墟中文網實時更新喪屍不喪屍最新章節並且提供無彈窗閱讀,書友所發表的喪屍不喪屍評論,並不代表聖墟中文網贊同或者支..
 九轉神龍訣 何謂強者?一念可碎星河!何謂弱者?一命如同螻蟻!楚軒天縱奇才,為救父親甘願自廢武魂,斷絕前路!守孝三年,終得九轉神龍訣,煉諸天星辰,踏萬古青天,鑄不朽神體!任你萬般法門,我一劍皆可破之!劍氣縱
九轉神龍訣 何謂強者?一念可碎星河!何謂弱者?一命如同螻蟻!楚軒天縱奇才,為救父親甘願自廢武魂,斷絕前路!守孝三年,終得九轉神龍訣,煉諸天星辰,踏萬古青天,鑄不朽神體!任你萬般法門,我一劍皆可破之!劍氣縱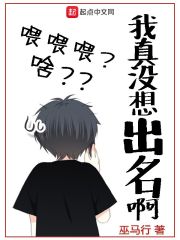 我真沒想出名啊暫時無小說簡介
我真沒想出名啊暫時無小說簡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