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一 拜神 幻海尋渚
一 拜神 幻海尋渚
 一 拜神 幻海尋渚
一 拜神 幻海尋渚
「少爺少爺!」,瀘州城沱江岸邊疾奔着一個小僕。他呼喚的主人是個十七八的少年,盤坐在一株大柳樹下,手捧着一本《脈經》,正看得聚精會神,給這仆童一擾,不耐煩道:「喂,秋生,叫你莫來吵我,你又亂咋呼幹啥子?」。那仆童正叫做秋生,上氣不接下氣,說道:「是雷大爺從閬中青龍會總舵回來了,老爺吩咐我把你叫回去,一道聽聽閬中的事情」。
讀書的少年嗤鼻道:「你一口一個雷大爺,他不過比我長三四歲,算的哪門子大爺?他別說從閬中回來,就是從皇城金鑾殿回來,和我又有什麼干係?」。
秋生咧嘴笑道:「少爺,你別老和雷大爺過不去。依我說,雷大爺對你這個兄弟可沒得說,他一介武夫,沒你念書多,有時性子急了,說你幾句,那也是一片好心腸」。
讀書少年道:「他是沒念過書,說是一介武夫倒未必,我看他心思機敏着呢,成天上躥下跳,在我爹面前扮成個好人」。
秋生面色沉了,道:「少爺,你這話說得可過啦。旁人看得清楚,你大哥雖非老爺親生,但無論是對老爺夫人還是對鏢局,那都是沒半點可說的。你這話對我說說也罷了,萬萬莫在外亂說,讓別人看笑話」。
原來這讀書的少年叫做雷秉,正是瀘洲城飛鷹鏢局的少公子。而秋生口中的「雷大爺」叫雷天垂,是雷秉之父雷立豐自小收養的義子。這雷天垂從小就懂事,精明能幹,心思縝密,頗有雷立豐之風,如今不過二十四歲,已隱隱然是飛鷹鏢局未來的接班人了。雷秉從來不喜武藝,和鏢局事務漸行漸遠,雷天垂急在心裏,常常說重話來激將責備他。二人本非親兄弟,長期口角之下,關係十分緊張。
雷秉逞口舌之快,說出這番孬話之後,已生後悔,又被秋生一責,便也不再言語,站起身來拍拍屁股上的土灰,道:「去吧,去吧,又聽聽他在閬中見了什麼大世面」。
雷天垂個子瘦高,年紀不大,已是一臉的絡腮鬍,他有意的蓄着,遮擋着這個年紀殘存的一點稚氣。雷立豐興致頗高,招呼道:「秉娃,快過來,你哥哥剛從閬中回來,讓他給你講講」。雷秉道:「說嘛,你說完了,好開飯呢」。
雷天垂一路風塵,剛狼吞虎咽了一大碗掛麵,又猛喝了幾口茶,往大椅上一坐,興高采烈又謙虛矜持道:「哈,也沒什麼好說的,不過總舵主和少舵主我都見到啦」。雷立豐驚得從座位上站起來,說道:「總舵主也見你了?他老人家近些年已經不親自過問青龍會會務,竟也見了你?」。雷天垂道:「爹,這等事我豈敢胡謅?總舵主說早聽聞爹您治理鏢局有方,又,又...」。雷立豐急問道:「又什麼?你別吞吞吐吐!」。雷天垂咧嘴憨憨一笑道:「又說你養了兩個成才的兒子,這才破例見我一次」。
雷秉心想,什麼兩個成才的兒子,分明只有一個罷。料必總舵主也只說了一個,你怕不好意思,硬生生捎帶上我了。雖這樣想,軟趴趴的身子不禁坐直了些。
雷立豐眉有喜色,道:「甚好,甚好,你繼續講」。雷天垂道:「總舵主又讚揚我們飛鷹鏢局每年進送的年貢遠遠超出了額度,表達了感謝,又和我說了幾句客套話,就走了」。
「那少舵主呢?」
「少舵主更客氣啦,搞得我還很有些不習慣,他和我對飲了三杯酒,還拍了拍我的肩膀,誇我身子結實,囑咐我好好跟着您學武藝學規矩」
雷立丰神色一變,驚道:「什麼?他囑咐你學規矩?你莫不是什麼地方怠慢了人家?」。
雷天垂忙搖頭道:「不,不,我說差了,沒『學規矩』這一句,我自己亂加的」。
雷立豐鬆了口氣,連連點頭:「好,好,你一句句轉述就成,自己亂加什麼?少舵主這些年從總舵主手裏接過大旗,年歲不大,可是賞罰得當,威望很高。你給他留個好印象,以後你還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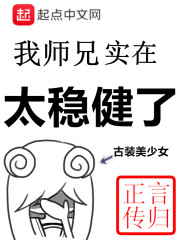 我師兄實在太穩健了 重生在封神大戰之前的上古時代,李長壽成了一個小小的鍊氣士,沒有什麼氣運加身,也不是什麼註定的大劫之子,他只有一個想要長生不老的修仙夢。 為了能在殘酷的洪荒安身立命,他努力不沾因果,殺人
我師兄實在太穩健了 重生在封神大戰之前的上古時代,李長壽成了一個小小的鍊氣士,沒有什麼氣運加身,也不是什麼註定的大劫之子,他只有一個想要長生不老的修仙夢。 為了能在殘酷的洪荒安身立命,他努力不沾因果,殺人 弄花師暫時無小說簡介
弄花師暫時無小說簡介 斬邪 八方亂,國將亡。百姓號哭於野,妖魔披衣冠據廟堂。弱冠書生,何去何從?仗劍而起誅鬼魅,提筆靜坐寫文章。手握乾坤,斬邪留正——一曲《正氣歌》,浩然起蒼茫。南朝書友群:200702009,熱烈歡迎新
斬邪 八方亂,國將亡。百姓號哭於野,妖魔披衣冠據廟堂。弱冠書生,何去何從?仗劍而起誅鬼魅,提筆靜坐寫文章。手握乾坤,斬邪留正——一曲《正氣歌》,浩然起蒼茫。南朝書友群:200702009,熱烈歡迎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