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第二章 外室獨寵?退婚另嫁世子爺請自重
第二章 外室獨寵?退婚另嫁世子爺請自重
 第二章 外室獨寵?退婚另嫁世子爺請自重
第二章 外室獨寵?退婚另嫁世子爺請自重
春雨敲打了一夜的窗沿,屋外漸漸泛起魚肚白,庭院深深的侯府某座院子,忽然響起一聲短促的驚叫。
外間守夜的爾晴披了外衫,快步入內,關切道:「姑娘可是又魘着了,這可怎麼行,等天亮還是請府醫來請個脈吧。」
他們家姑娘這一個月來,隔三差五便要驚叫着自夢中醒來,人都瘦了一圈兒。
等走到近前,見主子竟滿臉是淚,恍然一驚:「姑娘這是怎麼了,可是有哪裏不好?」
望着面前鮮活的貼身婢女,謝晚凝不可置信的死死咬住唇,直到感受真切的痛意,才喃喃道:「我做了個夢,太可怕了。」
「還是這段時間的那個夢嗎?」爾晴掏出帕子給主子拭淚,柔聲勸道:「姑娘莫怕,夢都是假的。」
謝晚凝怔怔握住她的手,忽然笑道:「是啊,都是假的。」
她斷斷續續做了半個月的夢,夢裏去剿匪的陸子宴平安回京,卻帶回一位外室。
聽說那位外室婢女出身,卻生的一副花容月貌。
聽說他對那位外室愛若珍寶,不惜違逆親娘。
聽說他為了那位外室欲登門退親,被路家老夫人以死相逼才願意履行婚約。
兄長親自上陸府要求他遣散那名外室遭拒後,爹娘勸她另覓良緣,可她卻如同豬油蒙了心般堅持要嫁給他。
他們青梅竹馬一同長大,自幼定下婚約,她從未想過自己會嫁給別人。
先前的夢,總是如隔薄霧,她並不當真,直到今夜。
爾晴死在她的眼前,是被陸子宴親口下令杖殺,夢中的畫面太過真實,夢中人的痛悔情緒似乎延續到了她的身上,叫她再也難以忽略。
這真的是夢嗎?
謝晚凝抿了抿唇,拭乾了淚,問:「陸老夫人昨日是不是說陸子宴來信了?他何時回京來着?」
「就這兩日。」她家小姐平日裏喚陸世子都是子宴哥哥,忽然連名帶姓的喚叫爾晴有些詫異,微微一頓,問道:「姑娘面色不好,今日可還要去武原侯府?」
陸子宴奉旨前去汴州剿匪,臨行前特意交代謝晚凝無事可去武原侯府多陪陪他年邁的祖母,和寡居多年的母親,叔母。
陸家滿門忠烈,陸子宴的爺爺、叔伯、還有他的父親,都接連戰死沙場,留下幾位女眷守着偌大家業,陸子宴是陸家僅剩的男丁。
對這根獨苗苗,不但陸家幾位夫人不肯放他去邊關,就連當今聖上也不忍百年侯府就此斷了香火,除了一些不算危險的剿匪,和查案任務外,從未派他上前線殺敵。
前兩年邊關告急,急缺能力出眾的將領,陸子宴幾次請旨,他得陸老將軍親手教導,兵法武藝皆不凡,聖上都咬死了不准,只道成婚後為陸家留下血脈,再談其他。
所以,謝晚凝才及笄不久,兩人婚期就已經提上了日程。
他們的婚事,不但陸、謝兩家關注,就連當今聖上也極為在意,夢中,成婚當日,宮裏幾位娘娘還給她添了妝。
明明是被所有人祝福的好姻緣。
結果她成婚不到半月,就得了劉曼柔有孕的消息。
謝晚凝閉了閉眼,不願再回想,她咽下再度翻湧的情緒,啞聲道:「去。」
謝、陸兩家乃通家之好,她同陸子宴青梅竹馬,陸家幾位夫人親眼看着她長大,待她不比親生女兒差,可是在夢中,隨着劉曼柔有孕後,她們還是對這位外室出身的貴妾緩和了態度。
反過來勸她既為陸家主母,那便該為陸家子嗣計,懂得賢良大度。
甚至在庶長子出生後,同意陸子宴將劉曼柔抬為二房平妻的請求。
陸家子息過於單薄,她們盼孫子盼太久,謝晚凝能理解她們的做法,但不代表她不會難過。
夢裏的她,真是難過極了。
婚前慈善愛護她的長輩,隨着一場婚禮,隨着妾氏有孕後,全變了。
 金玉良媛 林家的二太太大着肚子撒手人寰。林家四小姐投井自盡。幸得上天垂憐,四小姐被救了回來。可自此,天真爛漫的四小姐變得訥言。人人都說,四小姐一夜長大了。但只有香荷知道四小姐是失憶了。這是一個穿越女鬥倒
金玉良媛 林家的二太太大着肚子撒手人寰。林家四小姐投井自盡。幸得上天垂憐,四小姐被救了回來。可自此,天真爛漫的四小姐變得訥言。人人都說,四小姐一夜長大了。但只有香荷知道四小姐是失憶了。這是一個穿越女鬥倒 史上第一方丈 在一個禪宗幾近斷絕的現代世界,素問身為一寺住持,發展寺院,培養武僧,開辦武校,超度,抓鬼,種田。傳揚佛法,普度眾生,最後成為國師的故事。 施主我看你骨骼清奇,不如入我門來,放下煩惱,悟得超脫
史上第一方丈 在一個禪宗幾近斷絕的現代世界,素問身為一寺住持,發展寺院,培養武僧,開辦武校,超度,抓鬼,種田。傳揚佛法,普度眾生,最後成為國師的故事。 施主我看你骨骼清奇,不如入我門來,放下煩惱,悟得超脫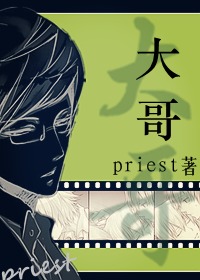 大哥 魏謙從來不知道自己老爸是誰,更不被母親待見,成天挨打挨罵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事,然而就這樣,他和他母親卻彼此仇視地活了下來。他十三四歲的時候,爹死娘死還帶着個只會流鼻涕的妹妹,因為無意中看到一
大哥 魏謙從來不知道自己老爸是誰,更不被母親待見,成天挨打挨罵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事,然而就這樣,他和他母親卻彼此仇視地活了下來。他十三四歲的時候,爹死娘死還帶着個只會流鼻涕的妹妹,因為無意中看到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