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第一百零七章 農場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
第一百零七章 農場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
 第一百零七章 農場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
第一百零七章 農場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
希娜站在樓梯口,全程圍觀了這場科維希克對克洛伊的單方面圍剿。
法堤瑪剛剛讓管家喊來了希娜,讓她幫忙看着克洛伊,如果克洛伊只是找科維希克鬧一鬧就讓她去,但如果這孩子轉頭就要回花園找那兩個水銀針的麻煩,就得攔着。
希娜靠着欄杆,看戲似的看克洛伊與科維希克唇槍舌戰。
事情發展到今天,並沒有多少出乎她意料的地方,唯一令她感覺詫異也感到疲倦的是克洛伊過於旺盛的精力——儘管她只比克洛伊大三歲,但在旁觀的時候她卻莫名感覺自己已經老了。
希娜捫心自問,自己生活里是否還有值得為之極度憤怒或極度悲傷的事物,然而想了很久,她也沒有答案。克洛伊再次開始尖叫大哭,家裏的許多人都已經開始為此感到厭倦,但這一刻,這哭聲卻勾起了希娜的自憐。她感到自己懷着某種願望,但她卻不知道這種願望應當是什麼。
從沒有哪一刻像這一刻,讓希娜感到自己正在被生活搓磨。
這一瞬的覺察像是多了一種觸覺,讓她第一次真實地觸摸到生活的無聊和庸常。即便她並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,但那種想要尋求變化的心情卻在突然間變得無比清晰。希娜抓緊了樓梯欄杆,心中忽然湧起一陣洶湧的浪潮。
發生些什麼吧,希娜心底也有一個聲音開始尖叫。
即便是災難,即便是不幸——但是無論如何,發生些什麼吧!
……
日落時分,尤加利獨自坐在農場邊緣的草垛上。太陽已經落下,但天卻沒有完全變黑。遠天的雲霞以一種無聲但磅礴的氣勢變幻着它的光影,在無邊無際的遼闊天空下漸漸暗淡。
「尤加利姐姐。」琪琪跑了過來,「吃飯嗎?」
儘管琪琪的聲音不大,尤加利還是被嚇了一跳,琪琪連忙過來拉她的手,尤加利笑着搖了搖頭,說沒事。
她站起身,隨手重扎了亂糟糟的頭髮,抖落上面粘着的稻草,剛轉過身,就看見不遠處還站着海澤爾。
「啊……」尤加利愣了一下,「你……你怎麼……」
「這地方真難找,」老人走到尤加利身邊,「我下午開車過來,結果直接開到後面那個鎮子上去了。」
「……我好像是聽她們聊到過要做新的路標,」尤加利低聲道,「不然是很容易走錯。」
「還好嗎?」海澤爾問。
尤加利露出一個苦笑。
海澤爾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將這場聊天持續下去。昨天她打過來的電話是由赫斯塔接聽的,海澤爾詢問能不能把手機交給尤加利,結果赫斯塔說,尤加利現在用不了電話,有什麼事她來轉達。
兩人就這麼聊了一會兒,從赫斯塔那裏,海澤爾才知道「脈衝音恐懼症」的事。據赫斯塔說,她們之所以把搬家的事情一下提到所有日程前面,就是因為原先的那間公寓臨街,偶爾汽車的連續鳴笛也會讓尤加利陷入恐慌。
「那她的飛行訓練怎麼辦呢?」海澤爾問。
「只能先緩緩了,」赫斯塔在電話里說,「您能不能也經常過來看看,我想如果有您陪她說說話,她可能也會好受一些。」
海澤爾有些猶豫,探望或聊天都可以,她打電話過來本來就是為了關心一下尤加利現在的情況。然而從赫斯塔提供的信息來看,尤加利似乎留下了點心靈創傷——儘管海澤爾也全程經歷了那一晚的恐怖襲擊,但這件事給她帶來的影響不算特別大。
在應承下這件事之後,海澤爾去網上搜了搜應該怎麼同尤加利這樣的創傷經歷者聊天,結果網上的建議讓她撓了一晚上的頭皮,那些林林總總的總結概括下來幾乎就是兩條:這也不能說,那也不能說。<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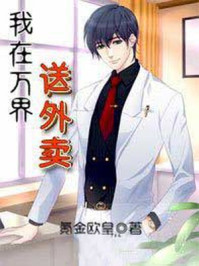 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
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 重生豪門:預言女王,拽翻天 【本文反套路、女主帥炸天】三個月前害她身敗名裂、抓她入獄,為了第三者要移她心臟的墨總裁回心轉意了。墨總將她抵在牆面,邪魅勾笑,低聲開撩:「原諒我,錢是你的,墨氏集團是你的,墨太太是你的,我也是
重生豪門:預言女王,拽翻天 【本文反套路、女主帥炸天】三個月前害她身敗名裂、抓她入獄,為了第三者要移她心臟的墨總裁回心轉意了。墨總將她抵在牆面,邪魅勾笑,低聲開撩:「原諒我,錢是你的,墨氏集團是你的,墨太太是你的,我也是 末日輪盤 當生命停止的剎那,葉鐘鳴回到了十年前,那個末日開始的下午。 是上天對自己的眷顧?還是又一次的懲罰?真的要重新體驗一次殘酷冰冷的末世嗎? 葉鐘鳴決定活下去,不為了別的,就為了那些曾經同生共死
末日輪盤 當生命停止的剎那,葉鐘鳴回到了十年前,那個末日開始的下午。 是上天對自己的眷顧?還是又一次的懲罰?真的要重新體驗一次殘酷冰冷的末世嗎? 葉鐘鳴決定活下去,不為了別的,就為了那些曾經同生共死